是我20岁青春懵懂的年纪。
这个年纪,本该是肆意飞扬的,像盛夏疯长的藤蔓,充满无限可能。
可我却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,像一只被无形之线牵引的木偶,每一个动作都僵硬而笨拙。
我尽力想做得更好,拼尽全力地踮起脚尖,渴望触碰那个被社会、被他人、被自己内心设定的标尺。
然而,现实总是一记冰冷的闷棍,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
人际关系像一团乱麻,学业或工作的压力如同永不停歇的传送带,对未来的迷茫更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霭。
我被一些不明所以的压力压得喘不上气。
那压力没有具体的形状,却无处不在。
它来自朋友圈里别人光鲜亮丽的展示,来自父母欲言又止的期盼,来自同龄人看似轻松的“成功”,更来自我内心深处那个永不满足、不断自我批判的声音。
渐渐地,我变得暴躁易怒,像一座一点就燃的火山。
对亲近的人失去耐心,对微小的挫折反应过度。
我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这样的自己了——那个曾经也会对着阳光微笑的女孩,被她自己囚禁在了情绪的牢笼里。
周围的声音嘈杂不停,每个人都长了一张嘴。
那些话语,轻飘飘地说出来,好像也完全不用负责。
那些批判的、质疑的、甚至裹挟着无形恶意的能量,并不需要真的从他们嘴里说出来。
当我凝望向他们的眼睛,在他们深邃的眼眶里,转动的眼球上,那微妙闪烁的光芒,那不易察觉的轻瞥或皱眉,好像都写满了对我的不满。
是我太敏感了吗?
或许是吧。
但我总能看见,我总不想看见。
每一次对视,都像是一场无声的审判,将我推向自我怀疑的深渊。
而每一次凝望你的眼睛——在我疲惫的想象里——我好像马上就要坠入无尽的深渊。
那深渊是我所有负面情绪的集合,是恐惧、是自卑、是深深的无力感。
你的眼神,像一面镜子,照出我所有的狼狈与不堪。
可是,奇怪的是,也正是这凝望,让我生出一种近乎固执的渴望。
但是我想看见深渊里的星星。
我想知道,在最漆黑的谷底,是否还有一丝微光,是独属于我的救赎。
你是否,就是那颗星星?
为了逃离这些目光,我走在路上,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。
视线所及,只有自己移动的鞋尖和灰扑扑的路面。
我下意识地用脚尖拨弄着路边的瓶盖,看它咕噜咕噜地滚远,发出空洞的声响,这微不足道的控制感竟能带来一丝短暂的平静。
走到路口,发现路边的井盖没有完全合起来,露出一道幽深的缝隙。
我鬼使神差地蹲下来,朝着那片黑暗,鼓足勇气大喊一声:“里面有人吗?”
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碰撞,带回空洞的回音。
我好希望里面能出现一个能陪我说话的声音,哪怕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存在,告诉我这一切并非我独自承受。
我蹲了很久,屏住呼吸倾听,连一只老鼠跑过的悉索声也没有等到。
巨大的失落感包裹了我。
站起身,一阵后怕袭来,我害怕真的有行人或小孩不小心掉下去。
于是,我近乎仪式般地,从书包里掏出那摞没什么用但当初却花了700块买的复习资料——它们像是我某种失败努力的象征——小心翼翼地盖在井口旁边,做了一个拙劣而显眼的提示。
这个举动很傻,我知道,但仿佛这样,就能弥补一下我内心那个巨大的、无法填满的缺口。
“我好想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,当个野人。”
这是我今年最大、也最真诚的愿望。
不用再理会任何规则、任何目光,只与山川草木为伴,让最原始的生存需求覆盖所有细腻的痛苦。
“明天要干什么呢?
如果还去那里的话,我还会遇到他们吧……”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向明天,带来一阵熟悉的焦虑。
“希望待会儿那条路上,我不会遇到那个奶奶。”
我可能有些奇怪吧,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是。
我喜欢穿的像个男生,宽大的T恤、破旧的牛仔裤、永远踩着一双看不出性别的运动鞋。
我穿的衣服,用那个奶奶的话来说,就是“不男不女”。
她每次见到我,那浑浊却锐利的眼睛里,总会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诧异和评判,有时甚至会嘟囔出声。
我不喜欢自己是个女生。
这个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像种子一样埋下,然后疯狂滋长的呢?
是小时候,爸爸指着妈妈的鼻子骂:“还不是你没用,生了个赔钱货!”
那一刻,我仿佛不是一个新生命,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,一个错误的性别。
是从妈妈每次和爸爸吵完架,都会把无处宣泄的委屈和愤怒转向我,哭着朝我怒吼:“你为什么是个女生!
你要是男孩,这个家就不会这样!”
好像从那些时候开始,“女性”这个身份,就与“错误”、“原罪”、“不值钱”划上了等号。
我就开始无比地讨厌自己,讨厌这个与生俱来的性别。
后来自己慢慢长大,身体出现了我不愿面对的变化。
我惊恐地发现,如果我穿着好看的裙子,稍微打扮一下,走在大街上,总会接收到一些异样的眼光。
那眼光不像奶奶那样首白的评判,却更令人窒息。
它们像无数根冰冷的、无形的银针,密密麻麻地刺在我身上,带着审视、玩味,甚至是不怀好意的窥探。
我甚至能产生一种诡异的幻觉,仿佛能感受到,当那些目光移开后,那些银针被拔掉的地方,会渗出细小的血珠,然后血会顺着皮肤的纹理,温热而粘腻地慢慢往下滑。
这种现象让我不寒而栗。
于是,中性甚至男性的装扮,成了我的铠甲。
它为我减轻了很多困扰。
我走在路上,不会再有轻浮的男生朝我吹口哨,不会受到某些男老师过度的“关心”和骚扰,这身打扮甚至可以让我看上去更加具有攻击性,像一只竖起尖刺的刺猬,警告外界保持距离。
我感到一种扭曲的安全感。
但其实,我心里明白,这些铠甲对于真正的痛苦来源——那些根植于童年、源于至亲伤害的内心空洞——来说,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
它们能挡住外界的风雨,却无法温暖我内心的寒冬。
我依旧孤独,依旧迷茫,依旧在深夜里被自我厌恶吞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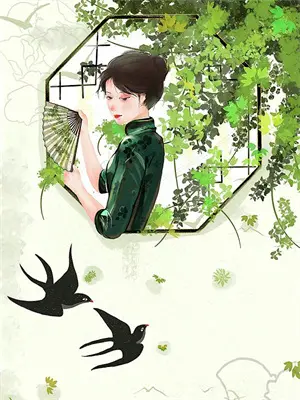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